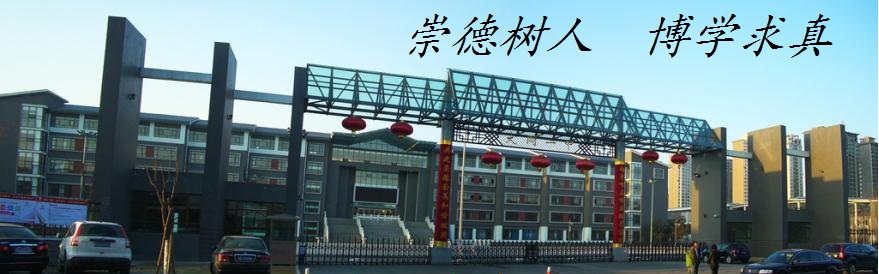回首望归途
一年将尽夜,万里未归人。
——《除夜宿石头驿》戴叔伦
图片
图片
坐公交车去
575班 宁渊超
“走啊,坐公交车去!”朋友一边说一边拉着我,半推半就地上了公交车。人不算多,我俩走着坐到了右侧后门附近的第一个双排座。仔细想来,我已有快两年没做过公交车了。
早以前出去上课的时候公交车是经常坐的,最开始是周六上午,于是我六点起床,来到公交车站在寒风中等待着迟来的公交车。坐在车上倒头就睡,全凭父亲把我叫醒。这个时候和我一样坐公交车的人原因大概差不多,车里一片死气沉沉,我甚至能看到几个熟悉的身影。就这样一辆辆车载着一个个梦和梦的主人,向着目的地驶去,司机除外。
对去时的记忆我大概是模糊的,后来时间改到了周六下午,我又睡不成午觉了,更没什么好印象了。但回去时的记忆却总是很清楚。
冬天是日短夜长的,等我下课的时候天早就黑了,等坐上车时人也变多了,我坐不上座,就在后门那站着。这个时候坐公交车的人和我的原因又是一样的。有结束了一天工作的疲惫的中年人,有夜生活刚刚开始的年轻人,有的家长带着孩子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,孩子们兴奋地聊着今天的见闻。我此时就看向窗外,看着一盏一盏亮起的路灯,街边商店的霓虹灯,心里默默记着商店的名字。我能看到大家的眼神里充满了疲惫但却又有一丝激动,我们都踏上了归途。我突然有点理解春运时人们的心情了。不过,这一切的一切都与司机无关,他能做的或许只有打开收音机。有的司机会放音乐,有的甚至会放单田芳。我几乎是在同一辆车上听完了《三侠五义》。
等车再开过几站,总会有那么一站——乘客们会像沙丁鱼一样涌出罐头。那时我和父亲就有座了。也就是我和朋友现在坐的位置。父亲不喜欢坐里面,就只好让我坐里面。他人有些分量,于是我总是被挤到了窗边。冬天天冷的时候,玻璃会结霜,外面一片模糊,我只能看见一团一团模糊的霓虹灯光,颇有些王家卫的感觉。有时候看着外面的一团光,我就知道车到哪了,我离家还有多远。我的心在跃动,我想起《柳林风声》里鼹鼠在和河鼠浪荡(姑且这么说)了许久后,第一次在雪夜里感觉到了家的气息。它知道阔别已久的,可爱的,温馨的,属于他的小家就在不远处。它就可以一扫疲倦,探寻着家的方向。
后来新冠疫情爆发,等我上了初三也不在去那上课了。我也就不怎么坐公交车了。现在想想,我或许怀念的不是公交车上的颠簸,而是回家的感觉。踏上归途,去一个总是愿意接纳我的地方,无论怎样。
终于,车到站了,我走下车,向家的方向走去。
温纳瑞斯的“归乡”
564班 郭振文
那是几十年前的一段往事了。
我扛着那架八磅重的摄像机,将镜头对准詹姆斯·乔治·温纳瑞斯,和台下百余架相机共同组成了灯光矛阵,团团包围了这位刚下战场的年轻人。他和二十一位战友一起,在战后通过总统先生的战俘自由遣返政策,申请在中国生活。
所有人都在等待,等这位小战士含着泪,控诉远东朝鲜战场上那群“恶魔”对他的欺凌,虐待,还有我们那神勇的军队是如何在朝鲜战场上杀敌的,尽管他们最终退回了美国。
“咳咳。”他清了清嗓子,台下的喧闹即刻烟消云散。灯光矛阵将他逼得更紧了,以至于这位年轻人不自觉的往后退了退。
“我在战俘营度过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。在这些日子里,深深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行动、言论所感动。”
会场一下由风平浪静变得波涛汹涌。震惊、慌乱、意外、气愤……记者们发狂了似的按动快门,拍照声、闪光灯充斥着整个讲台。
“他绝对是被洗脑了,”我身旁那个路透社记者嘟囔着,“早就听说苏联和中国掌握了心灵控制。”
“我们切断了志愿军的后勤补给线。志愿军战士每天都在吃玉米、高粱、咸菜。我们这些吃惯了牛肉、面包、奶酪、巧克力的美国战俘,开始都担心会受罪。然而,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,在俘虏营我们生活得非常好。志愿军组织车辆冒着美国飞机的轰炸,从国内运来大米、面粉、肉类为我们改善生活。”那个小战士接着说,仿佛台下的喧杂吵闹与他相隔着两个世界。
会场的秩序连警察都无法维护下去。一些警察开始遣散记者,拉起防护线,而另一批则冲向台上,架着温纳瑞斯离开会场。
震惊之余,所有人都把他当成了一个“叛国者”。人们讨论着,杜鲁门的战俘自愿遣返政策是多么荒唐,以至于他们没法处理这位即将动身中国的叛徒;东方人的心灵技术究竟多么可怕,能让一个美国人忘记家乡,要去建设那个一穷二白的中国?
我告诉助手扛着摄影机,自己追了上去。当我气喘吁吁地找到温纳瑞斯时,这个一头棕发,目光如炬的年轻人说:“朋友,有什么事吗?”
“我想知道……”我犹豫道,“我想知道你在战俘营究竟经历了什么。”
他爽朗一笑,然后又打开了话匣子。
那是我从未听到过的故事。碧潼战俘营运动会、志愿军和战俘的平等关系、战俘营授课学堂……他的目光越发澄澈明亮,不如我所见之军人一般。
我无法猜测眼前这位战士究竟是被心灵操控了,还是他真正融入了那个共产主义国家?
“所以,你真的要离开你的家乡,前往中国吗?”我最后问道。
“我在战俘营学习的时候,有个军官告诉我,中国古代有个词人这样说过:‘吾心安处是吾乡。’”
春花翻动,晨风吹拂,日光打在他脸上,印出斑驳的影子。我看着这位年轻人走向走廊深处,踩过斑斑点点的方砖,踏上对面归中的红毯。
真实,我从来没有探寻过的真实。
后来,当我们的总统在演说中称美军为“凶恶的狗”时,我又想起了温纳瑞斯和他的“归乡路”。
我筹划着再写一篇文章,名字就定作《最可爱的人和凶恶的狗》吧。
归途
573班 魏思宇
我们一直在奔跑。向前,向前。
我们从小便知道,征程无限,未来可期。
有的人摔倒了,再也没有起来;起来了,也只作原地徘徊。有的人,选择了继续前行。
不会痛吗?不会哭吗?还是过分坚强?是我们把眼泪藏到了不为人知的角落——越是向前,越是如此——仿佛这样,才不会被世人嘲笑。
我们知道古时文人墨客;我们从他们的笔下越过千年,相逢,相识,乃至相知。他们亦将人生视为一段旅途,或怆然涕下,或相顾无言,或以一蓑烟雨任尽平生——在这里,人生是为征程。
游子望乡,慨叹明月一轮——漂泊异地日久,心归故里情切。是挣扎在向前的路上,饱受风雨——由此转而望向归途。
归途,来时路,向着最初的地方。
“君问归期未有期”,是情怯,还是不奈何?其实我们都知道,回首望归途,同是路遥遥。更何况,有些路,惟进不退。
我们脚下的路可有归?我只知道,从不服输的我们,未曾将其列为选项。宁愿哭着奔跑,也不要笑着主动弃票。
我们守着深夜凌晨未熄的灯火,两点一线穿梭于只有路灯昏黄的街道,磨在题海里,计较,争论,只为眼前谜团一时明了。困意浓涌,昏昏欲睡,却总是要与自然相悖——一遍遍告诫自己:我不能倒……不同于古人,我们并不总在满是诗情画意的路上——我们自己的路,单调且枯燥。但这却是真真切切,是我们需要征服的漫漫长途。
是否曾问过:再向前,有什么?路的尽头,是什么?
也许有答案,但是也许每个人都不同。
我们走在同一条路上。
然后又各自选择不同的路。
曾经有过一段短暂的相遇和相伴。
我们都留恋有人相伴的快乐,我们都害怕失去同行者的孤单。可在选择的时候——出现了岔路口的时候,似犹豫,实决然。
我相信每个如此选择的人,都看得见远方,都听得见自己的心。不应该迷茫吗?可内心分明有一道声音,告诉自己,路的尽头,是繁花。
何为其然?
路之尽头,是梦之彼岸,是初心所向——
抵至此,征程是归途。